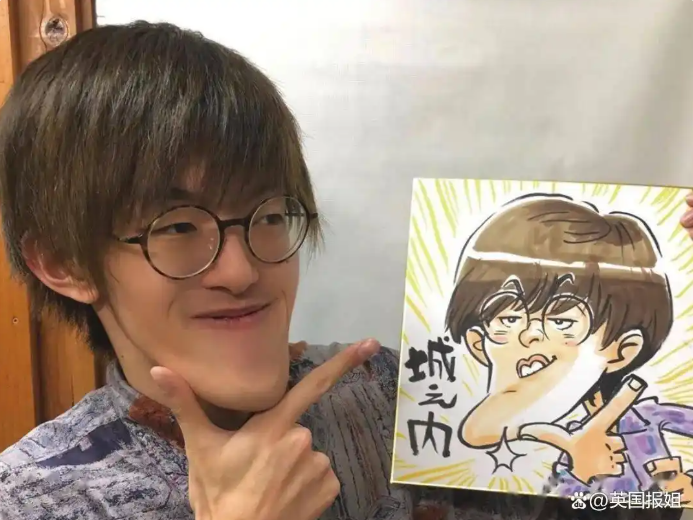![图片[1]-在经历了长达38天的干旱之后,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农民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降雨。-春天资源分享网](https://www.uctravos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8/7176f28a1420250810114615.jpg)
七月,上蔡县的一隅,干旱的玉米地映入眼帘,如同一幅苍凉的画卷。在这片土地上,岁月的磨砺塑造了一群守护者,他们与土地朝夕相伴,早已将自身融入其中,形成了与大地相契合的品格与心灵。然而,今年的旱情,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自五月底以来,天空失去了往日的温柔,变得狂躁不安。小麦收割完毕后,土地转瞬之间便干燥如石。玉米播种后,便开始遭受干旱的折磨。6月30日,驻马店市气象服务中心发布高温预警,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魏国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痛心疾呼:“此次河南旱情,堪称200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。”
上蔡县的大片玉米地,秆子枯瘦如柴,叶子因烈日炙烤而卷曲。徐青友,这位年过七旬的农夫,深知若天不降雨,待到十月,这片土地上的玉米产量将不足300斤/亩。他的语气中透露着无奈与焦虑,眼神如同干涸的土地,期待着生命的滋养。
徐青友是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农夫,他的身躯佝偻,个头矮小,肤色黝黑。在这副看似单薄的躯壳中,却蕴藏着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关节炎等难以言说的痛楚。他那指关节粗壮如老树根,是他对这片土地的执着与坚守的见证。他自称已年过七旬,就像脚下这片土地,表面上看去风平浪静,实则内里千疮百孔,有时即便是竭尽全力,也难以触及那些隐藏的隐患。
无奈之下,徐青友只得召回在驻马店工作的儿子徐守军,共同引水浇灌。为了保住土地的生机,父子俩的饮食变得简单:一个白面馒头,便足以支撑一整日的劳作。直至8月6日,情况才有所好转。河南多地陆续迎来降雨,徐家父子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甘霖。这场久违的雨水,他们等了整整38天。
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邵宇翔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,目前来看,平顶山、驻马店、周口、濮阳等地局部旱情已得到明显缓解。然而,面对持续的暴雨,农民们又担心庄稼会遭遇涝灾的侵袭。
在生机勃勃的玉米田旁,徐守军的存在似乎成了这片土地的守护者。他究竟能在村里逗留多久,他自己也难以预料。然而,他心中对父亲的记忆却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,历历在目——那是一位将一生奉献给土地的父亲,终日与泥土为伴,与耕作为伍。
2024年,河南驻马店的粮仓再次丰盈,总产量高达807万吨,仅次于其北邻的周口。这片沃土,得益于其平坦的地势和广袤的耕地,依靠小麦、玉米、花生的轮作模式,年年丰收,稳如磐石。然而,今年夏天,驻马店和周口却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为酷热的夏日。这股炎热,如同一位无情的判官,让徐青友这位老农几乎束手无策。
7月初,当干旱的烈焰无情地炙烤着大地,徐青友在绝望中拨通了儿子的电话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焦虑:“天气太热了,连一滴雨都没有下,地里的玉米就像被烈日折磨的孩童,无法挺直腰杆。至少每隔2-3天就要浇一次水,才能让它们活下去。”话语间,不难感受到这位老农对土地的深情厚谊,以及对丰收的殷切期盼。
挂断电话的瞬间,43岁的徐守军将餐饮店交托于妻子,匆匆踏上了回村的征途。他怀揣几节水管,犹如战士握紧武器,从驻马店市区一路疾驰,归心似箭。归途中,徐守军目睹了一幕幕惨淡的景象:大片玉米叶已枯黄,土地龟裂,仿佛被烈日炙烤得濒临死亡。唯有几株青翠的玉米,顽强地伫立在贫瘠的土地上,那是当地豪绅的地盘——得益于近水楼台先得月,他们才有能力灌溉这些宝贵的生命。
徐家,并无半点资本可言。距离村中抗旱井有500多米之遥,取水灌溉,必须遵循“本家、本姓、本村”的规矩。徐守军凭借着年轻时的勇猛,早早地赶往井边,抢先将水管接通。灌溉,是一项既费时又费力的事。500多米的管子灌满水,重如泰山,移动起来异常艰难。若是不停歇,最多也只能灌溉一亩地,另一亩地则不得不等待。于是,徐守军只能一段段地抬起管子排水,缓缓移至下一亩地,如此往复,直到夜幕降临,才堪堪浇完两亩地。
然而,当夜幕降临,浇过的地很快又干涸了。徐守军捏起一把泥土,泥沙从指缝间滑落,玉米依旧萎靡不振。干旱,如同一个无情的杀手,无情地扼杀着每一株鲜活的作物。徐家人,面对这令人窒息的绝望,不禁陷入深深的无奈:我们一直在努力,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。
村子里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仿佛陷入了一种单调的循环。那些家境殷实的户人家,凭借自家的水井,硬是抵御住了旱魔的侵袭,而那些依靠公用井取水的村民,却只能“勒紧裤腰带”,勉力维持着生活的希望。面对这严峻的旱情,村干部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在与时代周报记者的对话中,黄埠村的村干部无奈地表示:“我们竭尽全力了。井里的水虽然全天候通电抽吸,干部们甚至亲自上阵,引管送水,但天公不作美,不下雨,我们实在是无计可施。”
来源:里斯资源分享网 https://lismoxy.cn/ 尔德资源分享网 https://edvjjs.cn/